从简单的线条勾勒到逼真的数字绘画,人工智能绘图模型的能力日益精进,仿佛一位不知疲倦、灵感永驻的艺术家,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,它的诞生与发展,是一条融合了数学理论、计算机工程与人类创造力的漫长道路。
这一切的根基,源于一个名为“机器学习”的领域,早期,研究人员尝试教会计算机识别图像中的内容,例如区分猫和狗,这个过程需要为计算机提供海量已标注的图片数据,通过复杂的算法不断调整内部参数,最终让它学会归纳出“猫”或“狗”的特征,这项技术称为“图像识别”,是后来一切AI视觉应用的基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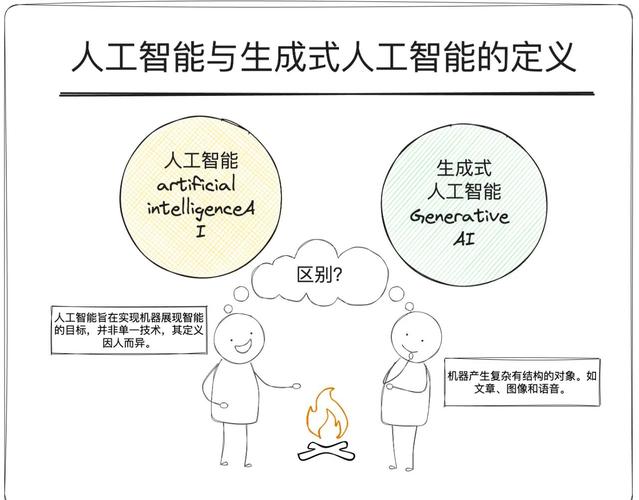
当机器学会了“看”,下一步便是“创造”,最初的尝试是使用一种名为“生成对抗网络”(GAN)的模型,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一场永无止境的艺术竞赛:场内有一位伪造者(生成器)和一位鉴定专家(判别器),伪造者拼命学习大量名画,试图创作出以假乱真的仿作;而鉴定专家则火眼金睛,努力甄别出真迹与赝品,两者在反复博弈中不断进步,最终伪造者的技艺炉火纯青,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作品,这便是早期AI艺术生成的主要原理。
GAN模型并不完美,其训练过程极不稳定,且生成的图像多样性有限,真正的革命性突破,来自于一种名为“扩散模型”的新范式,它的核心思想非常巧妙:不是直接学习如何画一幅画,而是先学习如何一步步地“去噪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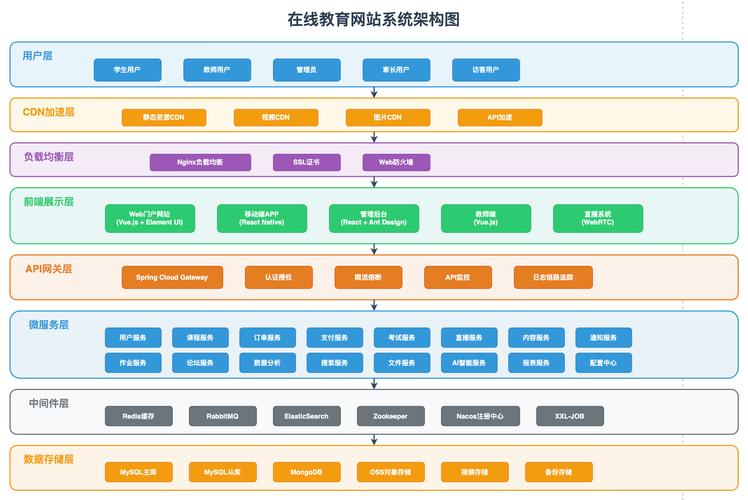
想象一下,你将一张清晰的图片逐渐加入噪点,最终它变成一团完全随机、毫无意义的像素雪花,扩散模型的学习过程,就是完整地记录下这个加噪的步骤,它进行逆向工程——学习如何从一团完全随机的噪点开始,一步步地去除噪点,最终还原出一张清晰、有意义的图像,在实际创作时,我们只需给它一团随机噪点和一个文本指令(一只穿着宇航服的柴犬”),模型便会运用所学,在执行去噪步骤的过程中,将文本描述的信息一点点“刻画”出来,最终生成全新的图像。
为了让模型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指令,另一个关键技术登场了:自然语言处理,诸如CLIP这样的模型,充当了图像与文字之间的“翻译官”,它在大规模“图像-文本”配对数据上训练,深刻理解了“穿着宇航服的柴犬”这段文字应该对应怎样的视觉特征,在扩散模型生成图像的每一步,CLIP都会从旁指导,确保正在被“去噪”的图像越来越符合文本的描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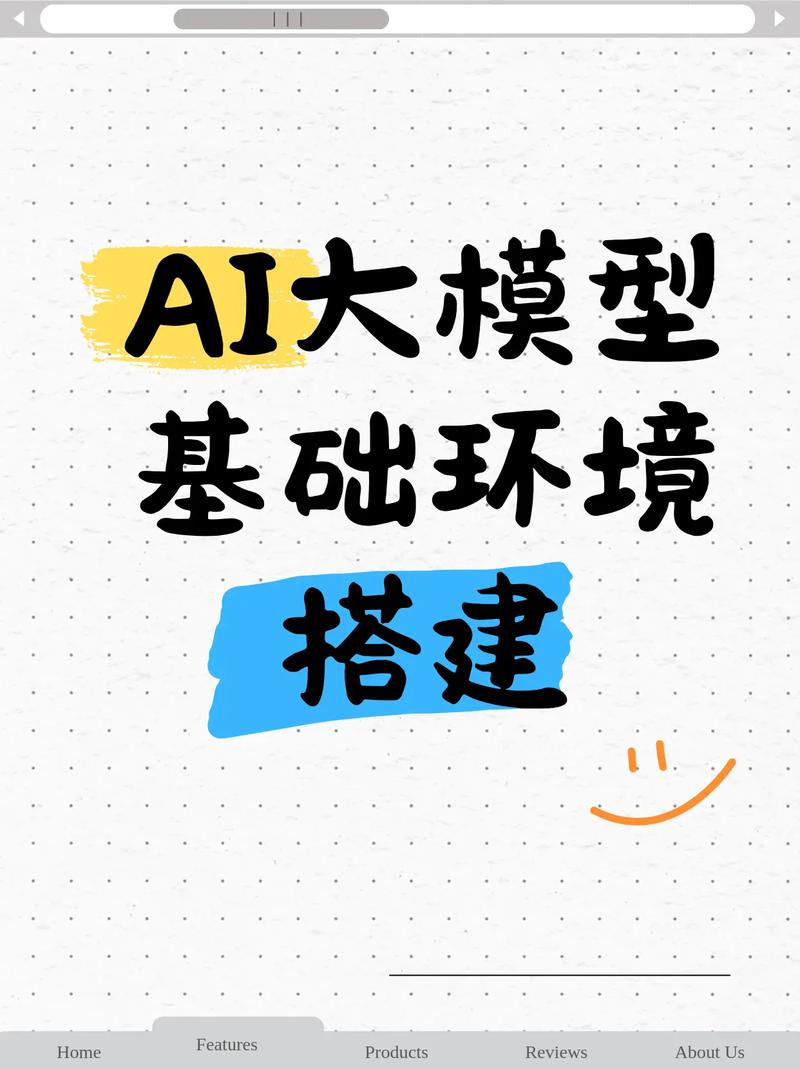
至此,一个现代文生图模型的核心架构已然清晰:它以扩散模型为强大的生成引擎,以CLIP这类模型作为理解人类意图的大脑,而驱动这一切的,是数以亿计的高质量图像-文本对数据,这些数据来自互联网的各个角落,经过严格的清洗和标注,成为了喂养AI艺术家的“食粮”,工程师们用巨大的算力,在超级计算机上对这些模型进行数周乃至数月的训练,不断调整数以十亿计的参数,最终才得以将它们压缩成我们可以使用的产品,例如Stable Diffusion、DALL-E 2或Midjourney。
从学术实验室里的一个数学猜想,到全球数亿用户手中的创意工具,AI绘图模型的演进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它并非替代人类的创造力,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和画笔,它的到来,降低了艺术创作的技术门槛,拓宽了想象力的边界,我们看到的每一张由AI生成的图像,都是人类智慧与机器计算力的一次精彩合奏。


